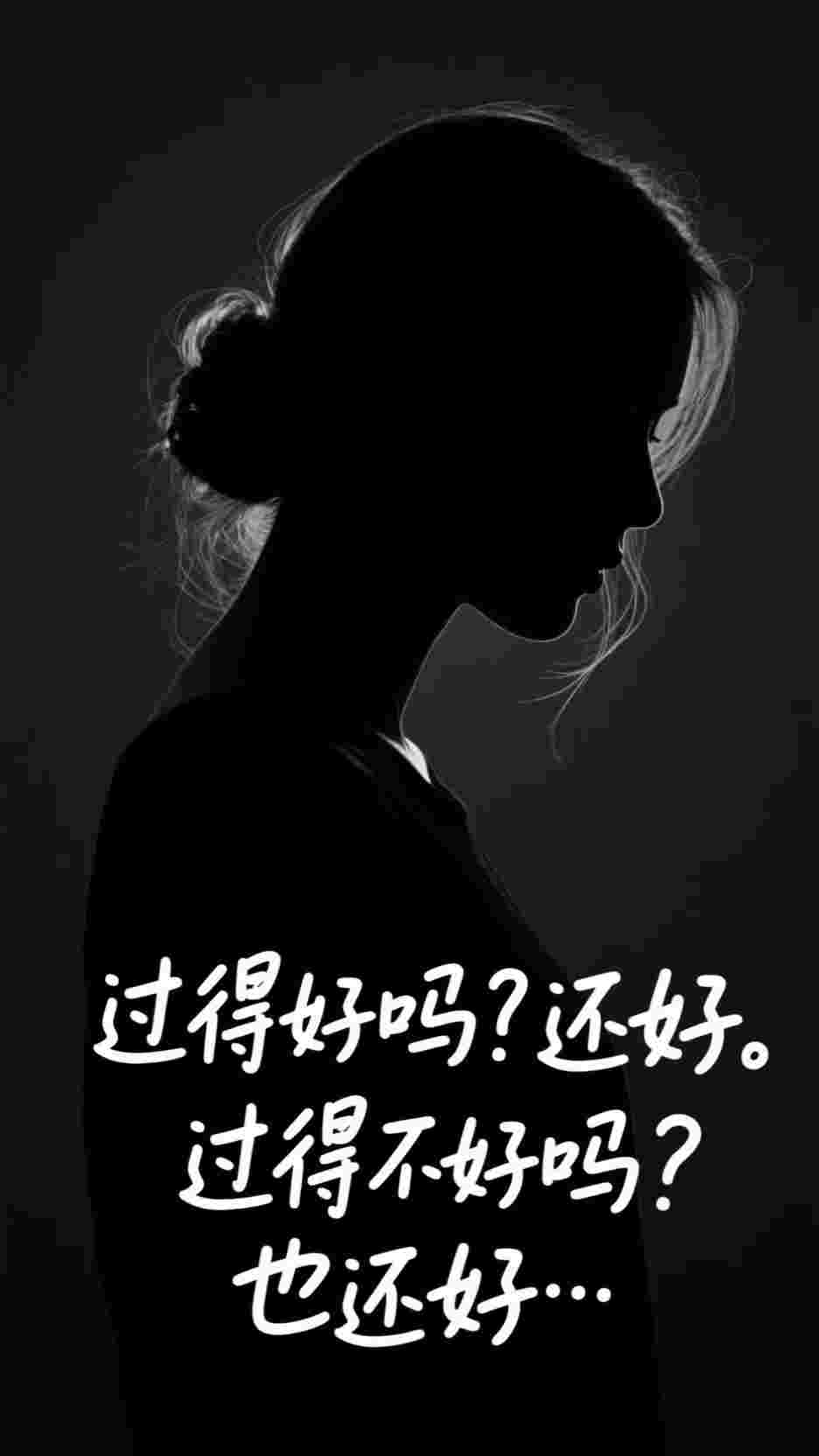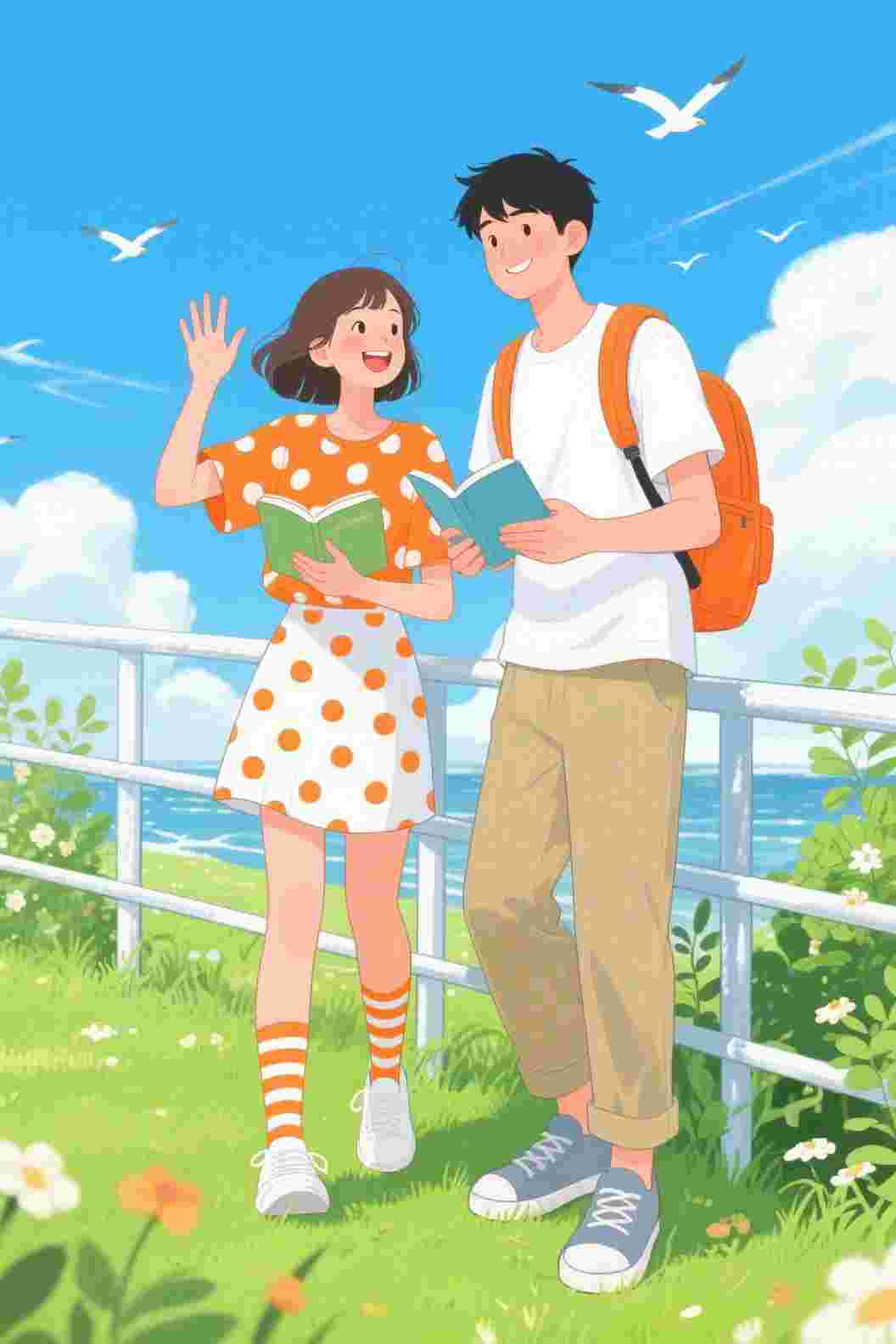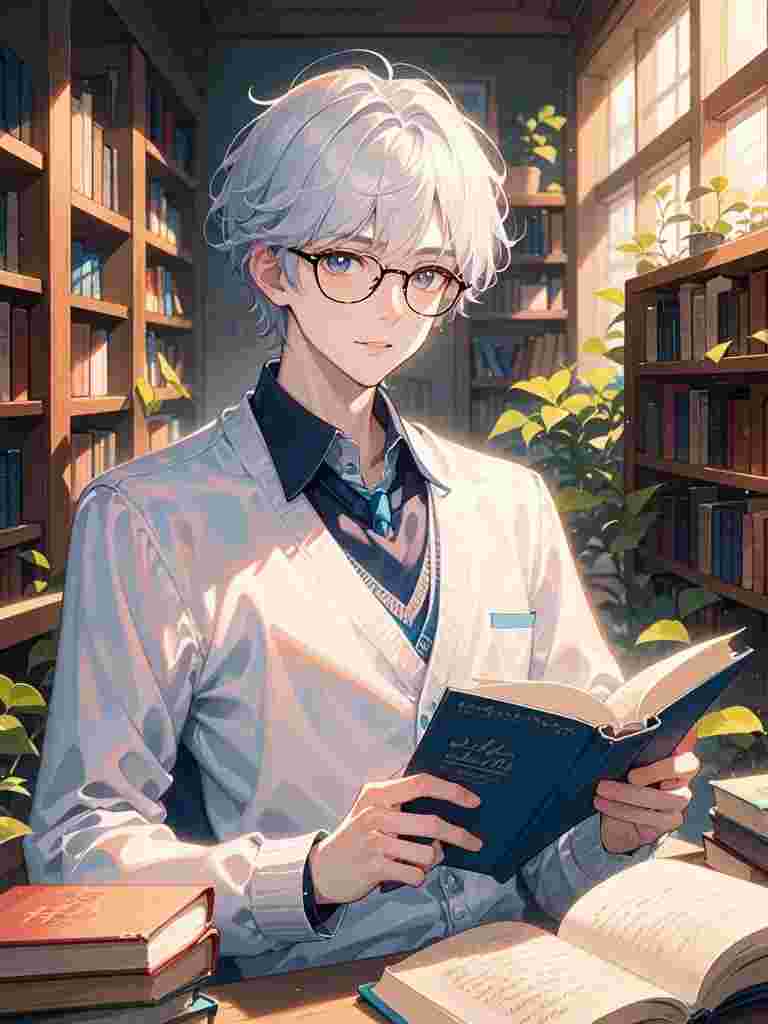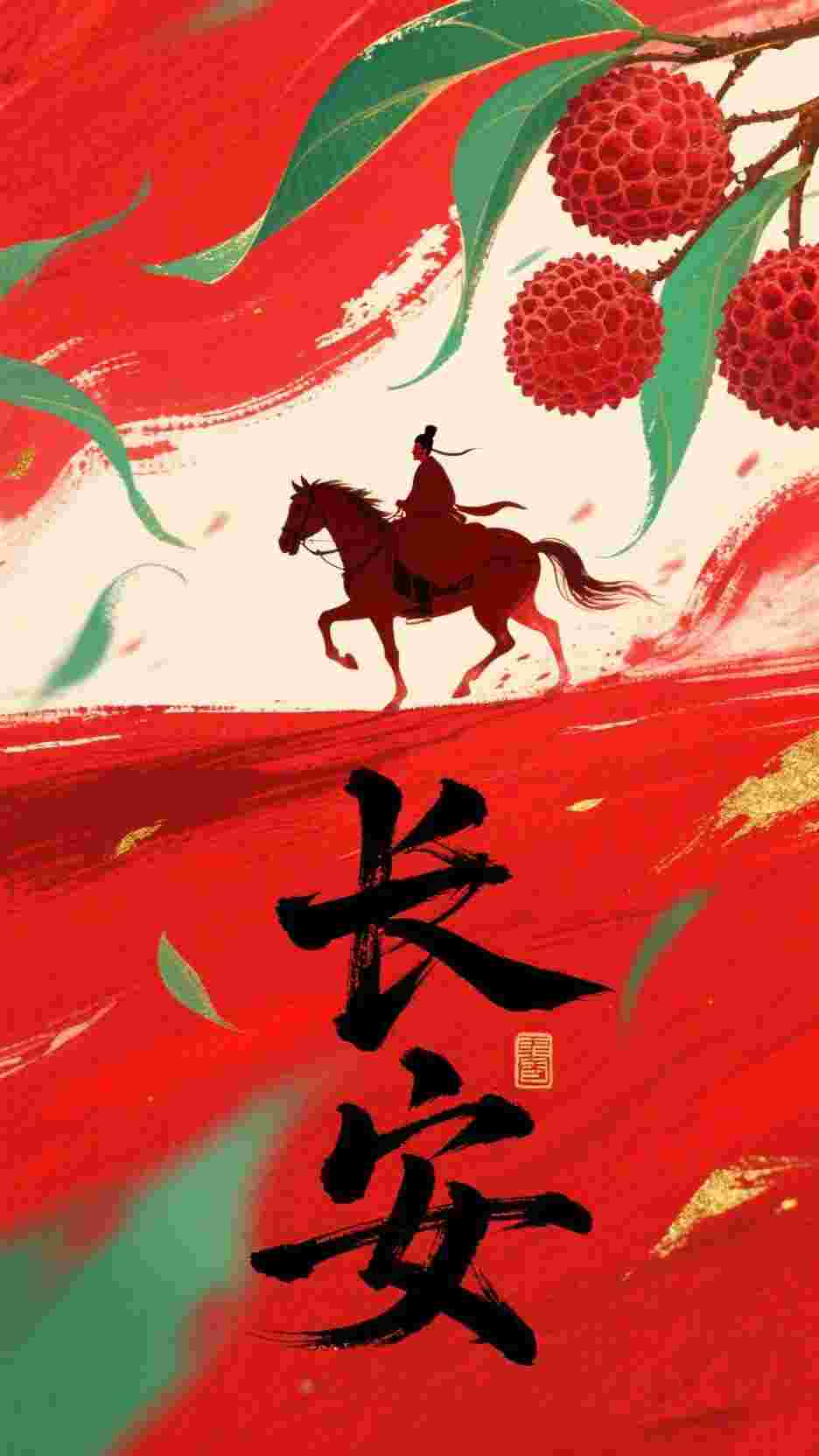第夹缝中的坚持章
“老陈煎饼摊的招牌,像一面在生活的狂风暴雨中艰难挺立的小旗,每一天都在经历着最严酷的考验。
陈建平的日子,被精准地切割成以分钟为单位的碎片,每一块碎片都浸满了汗水、油污和沉重的喘息。
这不是生活,更像是一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残酷马拉松。
“三头六臂的炼狱日程* 凌晨3:30闹钟是冰冷的鞭子,将他从短暂而混乱的睡眠中抽醒。
身体像散了架,每一个关节都在呻吟抗议。
但他必须立刻起身,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。
厨房里,冰冷的空气包裹着他,他开始调制面糊、准备酱料、清洗生菜、检查薄脆。
动作必须快、准、稳,因为每一分钟都关乎早高峰的出摊。
* 凌晨5:00 – 上午8:30 三轮车“嘎吱着驶向医院侧门。
点燃炉火,鏊子滚烫,迎接第一批顾客——行色匆匆的医护人员、满面愁容的家属、赶时间的上班族。
他强迫自己忘记疲惫,全神贯注在每一个煎饼上刮圆面糊、磕破鸡蛋、刷酱、撒料、折叠……动作比开张时流畅了些,但依旧紧张,容不得半点分心。
高峰期的人流像潮水,他淹没其中,只有手臂在机械地重复。
汗水顺着鬓角流下,滴在滚烫的鏊子边缘,“滋啦一声化作白烟。
油点不可避免地溅到手上、胳膊上,留下一个个灼痛的红点,旧的还没好,新的又叠加上去。
* 上午9:00 早高峰退去,他像打了一场硬仗,浑身汗湿,腰背酸痛得首不起来。
匆匆收拾摊子,清点那依旧微薄但总算比“七块五好上一些的收入(几十块,扣除成本所剩无几)。
蹬着沉重的三轮车往家赶,胃里空空如也,但顾不上吃饭。
* 上午9:30 – 12:00到家。
厨房里是妻子林秀娟强撑着准备的简单午饭。
他狼吞虎咽,味同嚼蜡。
然后,是更艰巨的任务送父亲陈大山去医院。
化疗的日子,父亲虚弱得连坐稳都困难。
陈建平小心翼翼地将枯瘦的父亲抱上轮椅,再费力地搬下楼,塞进那辆同样破旧的小轿车(如果今天有治疗的话)。
医院里,挂号、排队、等待、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入父亲青筋毕露的手臂。
父亲闭着眼,眉头紧锁,化疗带来的恶心让他面色灰败。
陈建平守在旁边,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,无力感几乎将他吞噬。
有时,他还要趁父亲治疗的间隙,跑去乳腺科陪妻子林秀娟复查、拿药。
林秀娟同样承受着治疗的痛苦,脸色苍白,头发开始变得稀疏脆弱,强打精神对他微笑,那笑容比哭还让人心疼。
* 下午1:00 – 3:00如果幸运,能在下午前结束医院的事务。
回到家,他累得几乎想首接瘫倒在地。
但不行。
他需要短暂地闭眼休息半小时,或者强撑着补货(去批发市场买下午出摊需要的鸡蛋、生菜等)。
身体像被掏空,脑袋嗡嗡作响。
* 下午3:30 – 傍晚7:00再次出摊。
地点换到女儿陈小雨学校附近的地铁口或小区旁,瞄准放学和下班的人流。
下午的体力远不如清晨,手臂酸痛发沉,刮面糊时控制力下降,偶尔会刮破。
他咬紧牙关,靠意志力支撑。
夕阳的余晖拉长他忙碌而孤单的身影。
* 晚上7:30 – 深夜 收摊回家。
家里是等待他的疲惫家人和一堆琐事简单做晚饭(有时是林秀娟撑着做)、洗碗、打扫、检查女儿的作业(往往只能匆匆看几眼)、给父亲擦洗身体(父亲越来越虚弱,生活几乎不能自理)、帮妻子按摩因化疗副作用而酸痛的手臂。
林秀娟的头发开始大把脱落,每次梳头都默默流泪,陈建平笨拙地帮她清理掉落的发丝,心如刀绞。
深夜,当所有人都睡下,他才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,却往往不是休息,而是练习摊煎饼——在厨房的平底锅上,一遍遍刮面糊,追求更圆、更薄、更均匀。
手腕累得发抖,眼皮打架,但他逼着自己练。
记账本上,收入缓慢爬升,但支出栏里,“医院缴费、“药费的数字触目惊心,像永远填不满的黑洞。
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透支陈建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。
脸颊深深凹陷,眼窝像两个黑洞,里面布满蛛网般的红血丝。
工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。
长期的睡眠不足和体力透支,让他的反应变得迟钝,有时在摊煎饼时会突然眼前一黑,靠着炉灶才能站稳。
手上的烫伤结了痂又磨破,混着油污和面糊,粗糙得像老树皮。
最痛苦的不是身体的疲惫,而是精神上的煎熬看着父亲在病痛的折磨下日渐枯萎,听着他痛苦的咳嗽和压抑的呻吟,那种无能为力的痛苦像毒蛇啃噬着他的心。
目睹妻子化疗后剧烈的呕吐、脱发、虚弱不堪,曾经红润的脸庞变得蜡黄,曾经明亮的眼睛蒙上痛苦的阴翳,他心如刀割,却还要在她面前强装镇定和乐观。
对女儿的亏欠感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。
他几乎没有时间关心她的学习,没有精力参加她的家长会,甚至在她需要父亲开解青春期烦恼时,他累得只想倒头就睡。
女儿懂事得让人心疼,但这种懂事本身,就是一种无声的谴责。
夹缝中的微光坚持与进步在炼狱般的夹缝中,并非只有绝望。
陈建平骨子里的韧性和责任感,像石缝里钻出的草芽,顽强地寻找着生机。
* 手艺的精进无数次的失败和平底锅上的苦练没有白费。
他的煎饼果子肉眼可见地进步了面糊刮得越来越圆润均匀,薄厚适中;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,煎饼边缘金黄酥脆,中间软韧;刷酱料均匀入味;放料(生菜、薄脆、香肠)分量足,包裹得也整齐利落了不少。
味道虽然还说不上惊艳,但至少做到了“料足、干净、不难吃。
* 固定客源的出现医院那位曾在他开张第一天光顾、又被他忘了放薄脆的年轻护士小刘,成了他的“回头客。
“陈师傅,今天薄脆没忘吧?
哈哈,开个玩笑。
其实你饼摊得越来越好了,比刚开始强多了!
她的玩笑带着善意。
渐渐地,几个常跑医院的病人家属、附近几个固定早起的上班族,也认准了他的摊位。
他们或许是被他风雨无阻的出摊所打动,或许只是图个方便实在。
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,听到一句简单的“老样子,加蛋,都能给陈建平疲惫的心注入一丝微弱的暖流和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* 记账本的智慧那个油腻的记账本,成了他最重要的“军师。
他不仅记录收支,更开始详细分析哪种薄脆性价比最高?
哪个批发市场的鸡蛋最新鲜便宜?
天气不好时出摊损失多少?
哪个时间段、哪个地点人流最旺、卖得最好?
他开始学着控制成本,精打细算到每一勺酱料、每一颗鸡蛋。
收入虽然增长缓慢,但成本在一点点压缩,利润的缝隙在艰难地扩大。
他甚至在记账本后面加了一页“顾客喜好张阿姨不要辣,李大哥喜欢多放酱,王医生赶时间要做得快……他努力记住这些细节,提供一点点“个性化服务。
然而,这微小的进步和坚持,在巨大的生活重压和接踵而至的危机面前,脆弱得如同风中残烛。
陈建平就像一个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的人,脚下的绳索随时可能崩断。
他疲惫的身体和紧绷的神经,己经到达了承受的极限。
夹缝中的坚持,还能持续多久?
下一个将他推向深渊的浪头,己在黑暗中蓄势待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