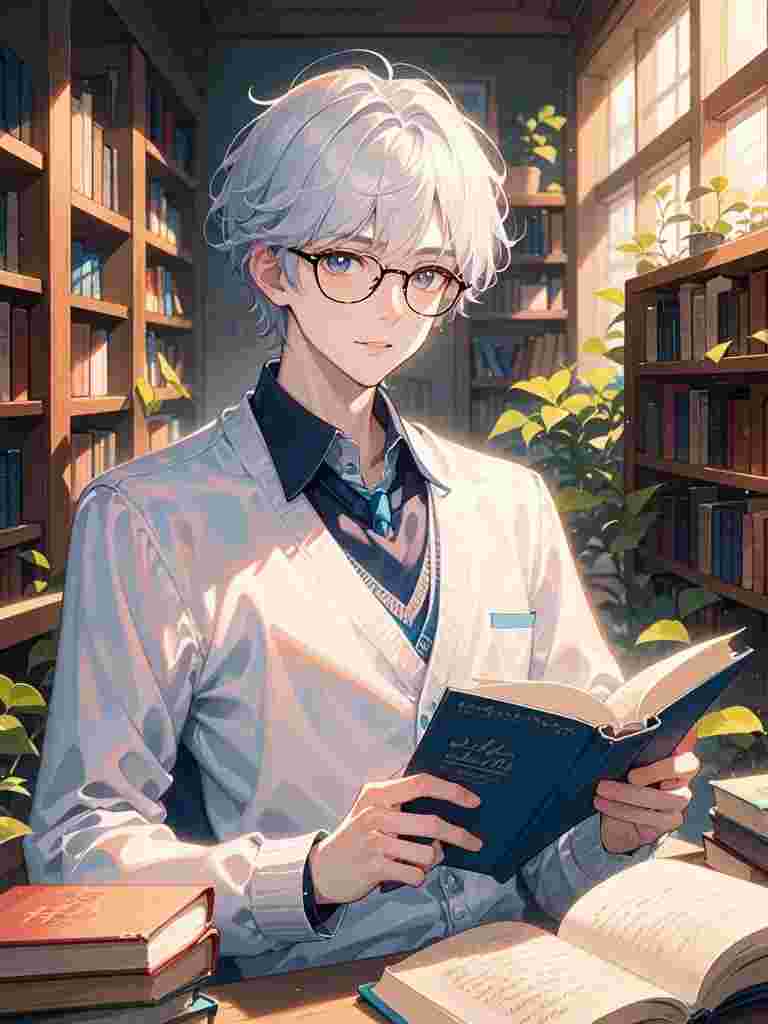第5章
4.
父亲身披玄色蟒纹披风,腰间的玉佩撞击出沉闷的声响。
“阿禾!
他踉跄着扑过来,玄色披风扫过燃烧的木柴,火星溅在他手背上,他却浑然不觉。
当看清我被火焰吞噬的裙摆下,那布满血洞与溃烂的双腿时,这位在苗疆执掌生杀大权三十年的王者,突然发出困兽般的呜咽。
“我的女儿,我的阿禾……
他颤抖着伸手,指尖在距离我脸颊寸许的地方停住,仿佛怕一碰就会碎掉。
我残存的左眼看见他鬓角的银丝在火光中泛白,那双曾教我射箭、为我别上银饰的手,此刻正抖得不成样子。
“王上认错人了! 沈宴捂着流血的脸颊嘶吼,血珠顺着他的下颌线滴在锦缎喜服上,像极了我流在水牢里的血。
“她就是个卑贱的董家女,连给嫣儿提鞋都不配,怎么可能是您的女儿?
父亲猛地回头,黑曜石般的瞳孔里翻涌着惊涛骇浪。
他缓缓站直身体,玄色披风在夜风里扬起弧度,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
“你说谁卑贱?
“我说她! 沈宴梗着脖子,血水糊住了他的眼睛。
“她未婚先孕,是苗疆的灾星,烧死她是天经地义!
话音未落,父亲腰间的匕首已化作一道寒光。
我甚至没感觉到他如何出手,只听见沈宴发出杀猪般的惨叫,半边脸颊的皮肉外翻着垂下来,露出森森白骨。
“在苗疆,还没人敢对本王的女儿说这种话。 父亲用沈宴的衣摆擦了擦匕首上的血,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。
“这一刀,是教你认清楚,谁才是这里的主子。
裴嫣儿趁乱往祭台后缩,绣花鞋踩在我滴落的血水上,滑出一道暗红的印记。
但父亲带来的银甲卫早已围成铁桶,长刀交叉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“我…… 我只是个外乡人。 她突然挤出怯生生的表情,裙摆上的金线在火光里闪烁。
“沈宴和董禾的恩怨,与我无关啊。
“无关?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冷笑,喉咙里涌上的铁锈味让声音嘶哑如破锣。
“裴嫣儿,你踩碎我外祖母婚服时,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左眼的血痂裂开,温热的液体糊住视线,我却能清晰回忆起她踩在婚服上的得意嘴脸。
“你说要用我的孩子给你的孽种陪葬时,也不是这么说的。
“还有沈宴…… 我转向那个在地上打滚哀嚎的男人。
“你说要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浸在血里祭奠她时,忘了吗?
5
每说一个字,就有一道血沫从嘴角溢出。
父亲突然按住我的肩膀,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,断裂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“王上明鉴! 裴嫣儿突然跪坐在地,双手合十作揖。
“是她自己诅咒我的孩子,是她先动的恶念!沈宴护着我,也是人之常情啊!
她的裙摆扫过我流产时凝固在地上的血污,那片暗红突然让我想起水牢里飘散开的血丝。
“人之常情? 父亲突然笑了,笑声里却没有半分暖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