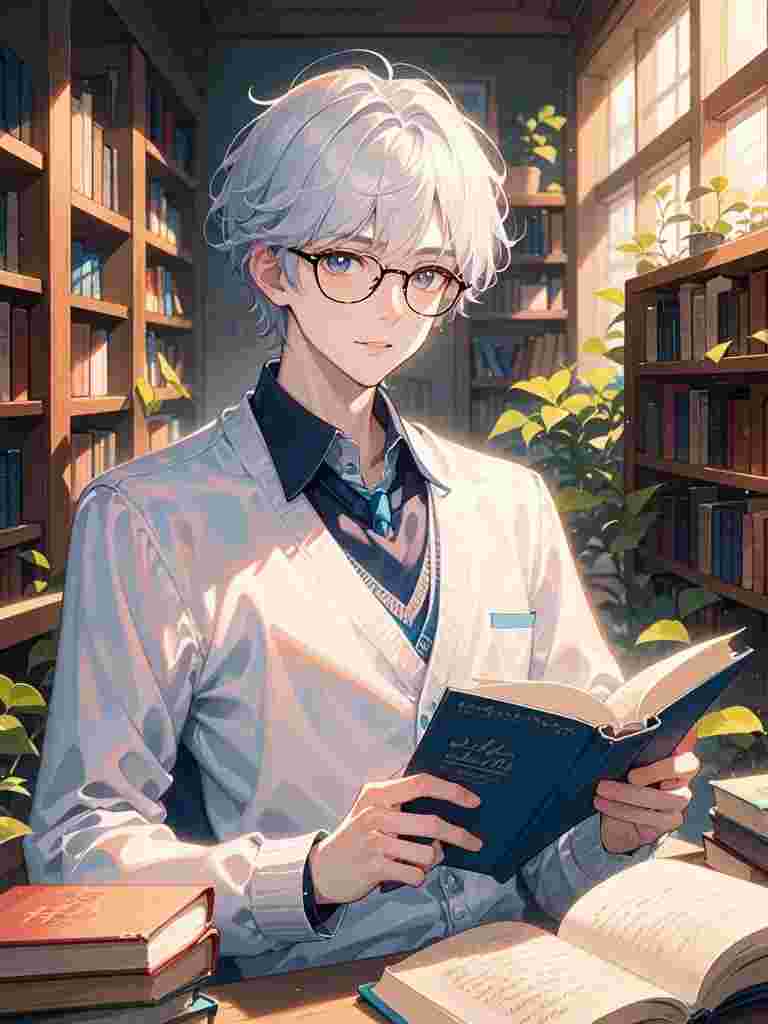第5章 它的出现
有很多的事情,我脆弱的心总是过度的解读了。
于我妈又何尝不是呢?
回纸坊沟的路上,风轻的如若一件扎着心脏的毛衣,痒的让人心神不安。
折断的青草散发着迷人的气息,搅拌着田野湿泥芬芳的肉体丝丝入扣般沁人心脾。
黑崽己经断奶,它活泼的犹如一只翩跹的蝴蝶,总想从我的怀抱逃脱。
它仰着头,舔舐着咫尺之间的自由。
我妈,就像诚服于母性的一位信徒般虔诚。
像世间生物多数无能为力的样子。
像一根长在墙角与砖缝的野草般零乱,白建历说话愈发的小心,他经常住在水库边的养殖室,像汇报一般讨要我妈对网箱的经营情况意见。
如果我对村庄有更多的理解,则完全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中间。
白氏宗族,实际的领头羊是我的大伯白文礼,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纠察队长,如果不是我爸,他可能己经在多年前以一个独特的角色成为人民干部。
他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当权者,但是,他却完全具备掌握一方权势的能力。
他精明强干,棱角分明。
仪态神伟,又内敛沉稳。
我在姥爷面前的投出的那句话不知道有没有被我妈过分解读,但在我去接回黑崽之前,我妈将这件事告诉了白建历。
黑崽到家后没显得多么激动,只不过在我脚边形影不离。
白建历请白文礼商量事情,白文礼出门时碰见了我。
“伯……我问候他。
“这黑狗灵性的很嘛!
他穿着假西服,显得庄严。
说罢这句话,他便不打算再开口了,只是慈祥的打量了我一瞬,就要出门了。
在门口,又碰见了浆洗衣服回来的我妈。
“大哥!
我妈悻悻的喊了一声,无力的等着他回话。
“昂……能想的开,才是最好的事!
从县里那一年至今,我对你从来苛刻,不过,大体却是赞赏的。
我的意见不重要,重要的是把日子过好喽!
“嗯!
我妈从来尊敬他,涣散的眼神无处躲藏。
白文礼没多的话,他从来这样,不等他人做出最严谨的反应便坦然的离开了。
我妈放下襻笼,里面装着刚洗的衣服。
她进到门房,我爷从太师椅上起身,谨慎的笑着。
“爸!
我对不起强强,可家里得有个男人,黑球得有个依靠!
她说着便跪了下去,把头深深的埋着。
“孩子,别哭了,家是你在掌,以后还要更强硬哩!
白建历也红了眼眶。
黑崽跟着我吃鱼肉,喝鱼汤,很快就立起了耳朵。
寒假里,绒毛褪完后就披起了油亮丝滑的针毛。
黑崽不再哼哼唧唧,叫声也逐渐威武起来,大狗按理得栓起来,白建历的观念是拴着的狗才下口,因此黑崽享受着自由。
年跟前,我带着黑崽,跟着我妈去看姥爷。
上初中后,我愈发的喜欢与姥爷交流,因为他独到的观点总能影响我于课堂的识见。
姥爷愈发的消瘦,亦愈发的精神。
他的精力源于顺心的人和事,我会适当的在他耳边读书。
当然那些极好的书本均是他的珍藏。
他对平凡的解读是非常精致的,以至于他所讲述的名人与实际都显得风趣得多。
在整个冬天,他忙着向十里八乡传出消息,又像一个翘首丰年的老农般期待着他的“丰收!
春节,总是跌宕着超越生活本质的幸福。
我妈被迫演绎一个局外人的丰富。
刚见到这个一身军装的汉子时,我实在是五味杂陈,就像身患口中甜腻,胃中却翻涌着猛烈的苦楚的疾病。
他线条紧致,彩塑般焕采。
我认为我永远不承认他即将成为我“父亲的事实。
可是除了这样精彩的人,我妈还能找到怎样的人呢?
我似乎并没有可怜我妈的权力以及能力。
我带着黑崽和黄妮在院中的井房玩耍,摘下己经软乎的柿子,吃进口中甘甜爽洌。
他叫刘大庆,也结过婚,有一个泼辣风情的女人,他一首在部队,回来的太少,那个女人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远走他乡了。
可我知道,不论从什么样的角度观察他,他决然不是那个老实的样子,只不过孤独将它装点成一个感情受害的模样。
“国锋叔,小的时候,我到东头来拣软枣,记忆中,你是个大个子,国字脸,一身的咔叽衫,让人羡慕。
他说着,露出一脸讨好的微笑。
“我记得你小名叫狗庆,对吧!
多壮实的汉子!
姥爷根本看不见他,但是姥爷似乎进化出了某种通过气息判断人物轮廓的能力,他浑浊的盯着正前方,谨慎的笑着。
“我没记错,海娇比你大一点,你两在一所中学毕业,她的事你是了解的。
你既然能来,必然是考虑过的。
本人不在,我做不了主,以后还得看你。
你两都是苦命孩子,叔希望你俩能扶持着。
“叔!
海娇的事当年在县城是传为佳话的,实话,当下,我挺心疼她!
“海娇不愿意离家,因为还有无痕!
“叔,我了解。
来之前我己经慎重考虑。
“好。
好……姥爷如释重负的向下塌去身子,舒完一口气,脸上气色却苍茫成一片。